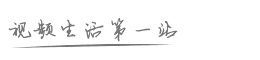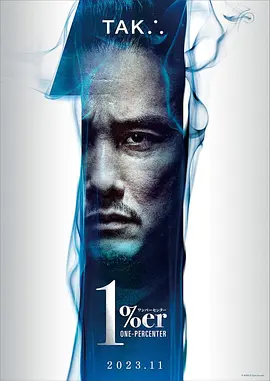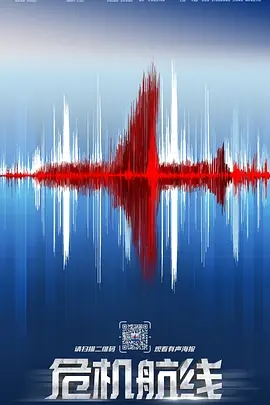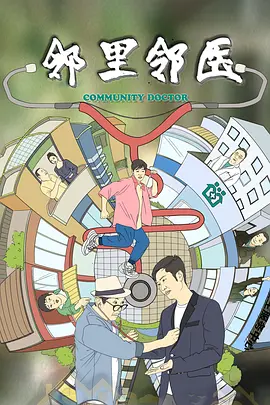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2018)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2018)
2018年台湾爱情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BD国语中字在线观看解说
◎译 名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More Than Blue
◎片 名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年 代 2018
◎产 地 台湾
◎类 别 爱情
◎语 言 汉语普通话
◎字 幕 中文字幕
◎上映日期 2019-03-14(中国大陆)/2018-11-30(台湾)
◎豆瓣评分 4.8/10 from 73341 users
◎IMDb评分 5.5/10 from 492 users
◎文件格式 x264 + ACC
◎视频尺寸 1280 x 720
◎文件大小 1750 MB
◎片 长 106 Mins
◎导 演 林孝谦 Hsiao Chien Lin
◎主 演 陈意涵 Ivy Chen
刘以豪 Jasper Liu
张书豪 Bryan Shu-Hao Chang
陈庭妮 Annie Chen
吴映洁 Gemma Wu
禾浩辰 Bruce Hung
游大庆 Da-Ching
石知田 Chih Tian Shih
黄丽玲 A-Lin
姚爱宁 Pi Pi Yao
◎简 介
唱片制作人张哲凯(刘以豪)和王牌作词人宋媛媛(陈意涵)相依为命,两人自幼身世坎坷只有彼此为伴,他们是亲人、是朋友,也彷佛是命中注定的另一半。父亲罹患遗传重症而被母亲抛弃的哲凯,深怕自己随时会发病不久人世,始终没有跨出友谊的界线对媛媛展露爱意。眼见哲凯的病情加重,他暗自决定用剩余的生命完成他们之间的终曲,再为媛媛找个可以托付一生的好男人。这时,事业有 成温柔体贴的医生(张书豪)适时的出现让他成为照顾媛媛的最佳人选,二人按部就班发展着关系。一切看似都在哲凯的计划下进行。然而,故事远比这里所写更要悲伤......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角色——Bonnie,她的喜感不仅仅来自于其单纯的性格和略为浮夸的肢体语言,更源于她独特的自我称呼方式——她从不用“我”指代自己,而是始终用第三人称Bonnie(自己的英文艺名)称呼自己。即便是在面对面的私人对话中,她依旧从不使用“我”这个代词。于是,听她谈论自己,就像是在听她描述另外一个人。
这样一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指称方式背后的逻辑是:将自我放置在一个“被审视”的位置上,以对待“客体”的方式审视和欣赏自己。这既是一种分裂,也是一种自恋。它意味着,自己无法以自我体认的方式描述自己,而只能将自己“客体化”,以此把握自身的感觉经验和情感体验。事实上,那个“客体化”了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虚构的自我,是一个理想化的自我,是经过伪装后的自我。
其实,Bonnie这个诙谐的角色,恰恰是这部影片所有人物的集中“隐喻”:每个人看上去似乎都很完美、很单纯,但完美的表象背后,是一个个已经抽空的自我。

“如果爱能解释,就不会有人为此而痛苦和悲伤”——作为影片开头的旁白,这句话与其说是对爱情的理解,不如说是在诱导观众以一种较为“宽容”的心态去理解接下来的剧情。其潜台词是:爱是无法解释的,如果你认同了这一点,你也就必须接受电影中你可能无法接受的内容,因为那些你无法接受的内容是不需要理由的。有趣的是,男主人公虽然口口声声强调爱情的非理性特征,却在具体的行动中以一种高度克制和理性的方式处理情感问题——张哲凯始终在努力地给宋媛媛安排爱情,为此他不惜用金钱去收买别人的爱情(要求摄影师Cindy离开牙医杨祐贤),收买失败后用自己的绝症道德绑架对方,其目的只有一个:要把一切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当当。
男主的行为背后,是一个被当代大众文化所普遍接受的爱情观念,即:“爱她,就要让她快乐。”这样的爱情观本无可厚非,但缺乏许多前提性限定条件:“让她快乐”的前提是要将对方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要了解“她”真实的快乐源泉,要以对方认为的快乐方式给予对方。然而,正如很多观众提到的,张哲凯所做的一切,是用自己所理的方式安排别人的幸福。他简单地认为对方会因自己的安排而幸福。这里且不谈“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陈词滥调,单就其心理动机而言,与其说张哲凯以深沉而克制的方式爱着宋媛媛,不如说是以想象的方式完成了自我的爱情救赎。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安排自己爱情的“剧情”走向,就像是一个观众,将“自我”客体化,欣赏着自己与宋媛媛之间的爱情故事而不顾忌对方的需求和感受,以自我欣赏的方式完成了关于爱情的美好想象,以自我感动的方式达成了对爱情的肤浅理解。而这,正如Bonnie的自我称呼一样,是一种分裂,更是一种自恋。
与张哲凯相比,宋媛媛则更加明目张胆,在明知道牙医杨祐贤有未婚妻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劳动人民迎难而上的精神,撬墙角、当小三,逆袭上位。更让观众难以接受的是,在骗走了牙医结婚证后,单方面退出了游戏,跟别的男人玩殉情。事实上,女主最后的殉情,仅仅为了制造悲情而悲情。看似在讴歌爱情的伟大,实则是在放大女主的脆弱,表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从情节上,我们很难捕捉女主殉情的动机——既然她深知自己爱的人临死前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她能幸福地活下去,那为何不顾爱人的遗愿却还要殉情呢?或许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她无法忍受失去男友后的孤独,只有经历相似的人才能理解相似的孤独,当这个人离开,剩下的只有一个孤独而空虚的自我,与其苟活不如轰轰烈烈地随他而去,至少在墓碑上还能象征性地将两个人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一起。可见,她与男主在一起的唯一情感支撑并非是纯粹的爱情,更多的是为自己排遣孤独寻找支撑。
这种解读虽然有过于主观化之嫌,但至少在接受层面上看,作为一部爱情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的情感逻辑确实难以博得大多数观众认同。观众之所以不愿为电影的悲情埋单,在于这部影片的男女主人公背叛了人性,看似很美,其实是卑。伟大爱情建立的前提是真实、自由、纯粹。而本片中男女主人公各自为他人做决定的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干涉他人婚姻的行为态度,以及最后无病呻吟的殉情行为,无不割裂了美好爱情的“表”与“里”的同一性关系。
这部电影对悲情的刻意营造,折射出当今时代每一个人空虚而匮乏的自我。很多人走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寻找的是一种悲情,准确的说是一种因匮乏而急需填充的表面化的悲情。这是一个悲情匮乏的时代,当代都市社会的繁忙、琐碎、重复,使我们难以从现实生活的平淡中掀起涟漪。生活越是平淡,我们对于悲情的诉求也就越发强烈。于是我们努力去在日常生活琐碎的一地鸡毛中制造悲情。这正如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每个人都急于寻找镜中的那个“自我”,然而每一次指认又恰恰是一次“误认”。悲情的匮乏从某种程度上反证了当代社会自我价值的“中空”。幸福和成功或许只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判断,人生真正的悲剧不在于经历了多少痛苦和挫折,而在于对原有信念的背叛,对自己控制命运决心的背叛。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充满悲情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其悲情的一面。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生命的流逝,一个个家庭的悲剧。我们反思每一个悲剧,反思他们的成因并联想到自身,由此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焦虑感。重压之下,于是我们逐渐走向了“犬儒主义”,其特征是要看穿、看透,同时却无所作为且不相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希望。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价,恰恰是当代这一文化语境的折射。这种被营造出的催泪情绪,是该片既成功又失败的地方。

殉情故事背后的解构崇高
与《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各种差评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相似的词汇:“无病呻吟”“矫情”“刻意煽情”。尤其是殉情这一桥段的呈现,让不少观众难以建立情感认同,并认为这是“老套剧情”的再次翻版。难道殉情故事已经感动不了我们了吗?抑或影片在呈现殉情故事时的方式有问题?
正所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中西文化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无论是中国的《梁祝》《孔雀东南飞》,还是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少年维特之烦恼》,不免都会以“殉情”为结局。殉情故事的核心,是歌颂恋爱双方敢于突破的勇气和对爱与自由的向往。它所探寻的是人类情感的纯粹性所可能达到高度。它将爱情放置在功利世俗的对立面,在成就伟大爱情的同时,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
俄国著名结构主义理论家普罗普在其《民间故事形态学》中,将民间故事划分为诸多角色功能,并将其作为叙事结构的基本单元。在普罗普看来,不同类型的民间故事有着较为稳定的角色功能及其秩序。借助普罗普的角色功能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把中西方较为经典殉情故事划分为四个较为清晰的行动序列:(1)男女主人公相爱;(2)爱情遭到外在因素干涉;(3)男女主人公一方自杀;(4)另一方殉情自杀。将这一序列简化,可得到“相爱——干涉——殉情”的基本叙事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殉情与其说是对爱情的坚守,不如说是对爱情纯粹性和超越性的一种确证。爱情所遭到的外在干涉,往往由世俗化的传统道德、宗法伦理、家仇国恨所承担,而殉情行为则是以摆脱世俗干涉的方式成就爱情的超越性。故事通过对世俗化因素的否定和扬弃,提升了爱情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在这一“正——反——合”的结构中完成了爱情主题的升华。
殉情的理想往往由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所组成:破坏与创造。破坏的,是肉体及其牵涉的世俗阻碍;创造的,则是灵魂及其代表的自由爱情理想。在这一相反相成关系背后,是一种“灵肉分离”的信念,即:肉体的消解无法阻挡灵魂的自由。于是在传统的殉情故事中,对待肉体的态度往往是不屑的,也正是在这种不屑的态度中,殉情的超越性才具有了能。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虽然在整体上基本承袭了传统的殉情故事的叙事模式,但在“干涉”这一关键环节上发生了变异。根据故事设定,男女主人公所面临的阻碍有且仅有一个:癌症。癌症意味着生命的有限性,它给男女主人公所造成的阻碍,仅仅停留在情感时间长短这方面,它恰恰源自于二人关系的内部而非外部。因为注定要分离,所以爱情始终只存在于彼此的想象中;因为相爱的期限注定是短暂的,所以任何一方无法给对方一个直到永远的承诺。
与其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如说这是一个爱情“断念”故事。至少在表面上,男女双方始终未能相恋,而阻碍这一恋情发生的,是因生命的有限性而导致的天长地久爱情理想的破灭。这恰恰是对传统殉情故事“灵肉分离”信念的背叛。在影片的潜在观念中,肉体存废不仅未能成为爱情所无视的对象,相反恰恰成为了爱情的阻碍。这与传统殉情故事有着根本上的差异:传统殉情故事中,肉体所支撑的仅仅是表面化、物质化、欲望化的爱情,而真正提升爱情境界的,是抛弃了肉体实存之后的深层性、精神性、无功利的爱情。在这一“深”一“浅”的对比中,爱情的超越性和永恒性得以体现。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则恰恰相反,男女双方一直纠缠且的,是肉体生命能否长久的问题。男主之所以刻意安排女主的感情,就在于他知道女主如果得知病情后无法接受进而跟他一同死去,男主所认为的幸福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所以无论女主嫁给牙医是否产生真正的爱情,只要女主还活着,总比死了好。同样,女主之所以在得知男主病情后继续配合男主的安排,就在于她深刻地理解男主的这一用心,既然男主生命所剩无多,那么以他希望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总比让他留下痛苦更好。这一切背后的逻辑是:肉体的永恒性是爱情的保障,爱情终极理想就是两个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如果肉体上的永恒无法实现,那么精神上的爱情就不能产生。于是,殉情故事本应具有的超越性和崇高性被影片解构,使得同样是殉情故事,《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与传统故事相比很难让观众建立起情感认同。
不仅如此,《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情感线索缺乏逐层递进的情感逻辑。影片中男女主人公一个被家庭所抛弃而另一个则因全家丧生而成了孤儿,这使得传统殉情故事中起干涉作用的世俗因素因二人的“孤独”身份而消失了。于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直接面临生死考验。传统殉情模式中从世俗层面否定上升为超越性爱情的升华过程荡然无存。影片从一开始的情节设定上就未能形成本应具有的超越性。为了给最后的殉情进行充分的情感铺垫,只能在叙事视角上做文章:先以男主视角,讲述其为了爱情所表现出的牺牲和成全以及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后转换为女主视角,呈现其为了顺应男主而作出的隐忍和让步,试图在视角的转换中叠加情感的浓度。遗憾的是,故事虽然几经反转,但一直停留在“情感/生死”这一层面的矛盾关系上,缺乏以往殉情故事中从世俗性上升到超越性的递进结构。对情感理解的层次性的单一和重复,导致影片在不断强调爱情的生死考验中延宕了观众的情感认同。这也是影片难以达成其悲伤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苦情传统背后的情感宣泄
从2017年《前任3:再见前任》中以“低幼化”的方式处理情感的现代都市青年,到2018年《后来的我们》中将事业成功贬损为前任离去后惩罚的中产阶级群体,再到2019年《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将自私爱情包装为超越世俗的殉情之美,无不折射出中国当代青年男女面的爱情观以及面对情感时的焦虑态度。这种焦虑表现为:既要追求纯粹的爱情,相信爱情的力量可以胜过一切,却又不愿为这份追求埋单;既要在想象中寄托超越性的爱情理想,却又在现实的无奈中为自己的私自寻找借口。
稍作辨析,会发现这三部情节和内容甚至是主题都相去甚远的三部作品,在其社会接受和情感态度上,包含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中国最“古老”的电影情节剧类型——“苦情戏”的基本模式(《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甚至在影片宣发中就将流泪和宣泄作为影片的核心“卖点”)。与传统那种以破碎家庭、破碎婚姻、家庭苦难为题材“苦情戏”不同,上述三部电影是以呈现爱情“遗憾”的方式达成其“苦情”效果: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基本毫无外在因素的阻碍,却因各种阴差阳错、不明所以的“遗憾”导致了爱情未能修成正果。透过种种故事的表面,不难看出,这种“遗憾”,源于一个古老而又世俗的爱情观:将婚姻视为爱情的最终目的和理想结果。
这种观念本身并无可厚非,但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其置于“纯爱至上”的故事外壳中,就会隐约显现出内在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故事试图呈现的是一种超越性的爱情观念,这种爱情化为亲情甚至达到了一种超越普通亲情、爱情的更高境界。这种在特殊情境下生成的特殊情感,本应使得一切世俗化的衡量标准都黯然失色。而另一方面,男主与女主的潜在诉求,却依旧是以结婚为最终理想,甚至在二人已经明确无法结婚的情况下,男主女主必须要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完成了其象征性的“婚礼”(男主给女主挑婚纱时的一张“婚纱照”)。

无需赘言,苦情戏的社会功用,恰恰是以充盈的悲苦和眼泪,成功地负载并转移社会的创伤与焦虑。《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通过苦情戏所唤起的廉价且合法的泪水,释放现实中由孤独感和纯爱观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巨大的失落和绝望,将它转化为一份“超越人间真情”与“珍惜身边人”的安全情感。从这个意义上看,《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之所以在台湾和内地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票房奇观”,是有着其广泛的文化基础与社会背景的。
当今时代,人类开始进入独居社会,美国纽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所说的“单身社会”正在成为一个普遍化的现实。独自生活的人更容易拜访朋友或加入社会团体,他们更容易聚集或创建有生气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准确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一个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社会,转变成了允许人们将自己才能最大化的社会。这一变化,直接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婚姻的理解。一方面,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了独立生活的资本和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爱情意义不再简单地是为了世俗生活,其价值必须被不断拔高。另一方面,社会又让每一个人成为了“原子化”个体,而人类的社会属性和传统的家庭组织方式要求个体必须在特定的社群中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虽然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可以把个人分享和大众传播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通过即时通讯、社交平台与外界保持联系,但这一切所支撑的仅仅是独居生活的物质性外壳,至于其背后的精神孤独,则只能被放置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于是,婚姻和爱情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组织方式必然性地承担了逃避精神孤独、维系传统家庭代际观念的作用。我们不愿接受被世俗化的婚姻,更不愿接受功利化的爱情,但爱情和婚姻又是当今时代青年男女摆脱“原子化”孤独的一种重要方式,对爱情崇高诉求又降低到了最原始的情感诉求中:摆脱孤独。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另一个潜在的情感逻辑,就是对孤独的拒斥。正如影片一开始所说:“人一旦习惯孤独,是一件比悲伤更悲伤得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因孤独而始,又以各自的孤独而终。这也是这一殉情故事的“不纯”之处:因失去亲人而导致的孤独,本应由亲情来填补,而男主与女主却以一种“类似爱情”的方式填补孤独,使得这一所谓的“爱情”具有了某种功利性意味。又因为这种功利性会有损爱情超越性,于是二人始终坚守爱情的纯洁性(影片中维持这一纯洁性的方式是反复强调二人性关系的空白),保持着“友谊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一起走过人生的16-30岁。
不得不说,影片虽然反复强调对孤独的拒斥和对纯粹爱情坚守,但其对于孤独和爱情的理解始终停留在表层面:只要有人陪伴就不是孤独,只要没有发生性关系就不算是爱情。这种靠表面化、外在化的证据来证明情感真实性的方式恰恰说明了情感的空虚和自我的缺失。事实上,是不是爱情,只有靠双方真实的情感体验才能证明;孤独不孤独,也只有自己的内心才能说了算,与是否有人陪伴无关。
男女主人公的从相识到相爱再到最后殉情的情感线索,给观众呈现了一个温馨而又甜蜜的“精神镜像”。虽然少有观众能有与男女主人公一样的经历,但观众却能从二人的孤独处境中指认出自我——那个在大都市中独居的、空虚的、孤独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以一种“苦情化”方式,成功地完成了当代社会群体性焦虑的宣泄和转移。
Tags:爱情陈意涵刘以豪张书豪陈庭妮吴映洁